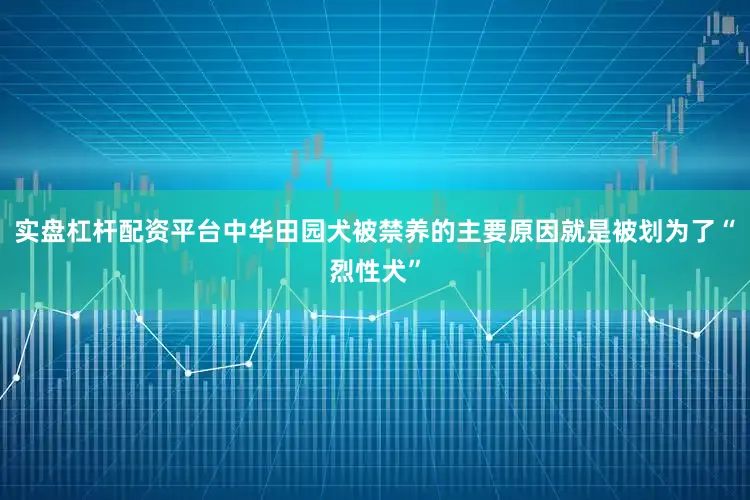黄河岸边的三弦说唱
七月的吕梁山,黄土坡被烈日炙烤得蒸腾起滚滚热浪。在离石区坪头乡马青局村那座饱经风霜的老戏台上,薛卫滨左腿绑着褪色的竹板,右膝扣着磨亮的铜铲,三根琴弦在他粗粝的指间翻飞跳跃,铮铮弦音裹着热浪,撞向台下举着手机的乡亲和直播间滚动的弹幕。“凑合着唱一段!”他咧嘴一笑,醒木“啪”地拍落,七字韵句便裹着热浪撞进沟壑。
“凑合”二字,像烙印,浸透了薛卫滨四十余年的人生。
薛卫滨和徒弟高彩芳(左一)、秦小艺(左二)、刘艳龙(右)在工作室排练节目。
黄土地里的“塞牙缝”与“地窝子”
1983年,薛卫滨出生在临县湍水头镇沐浴村的一孔土窑里,兄弟五人中他排行老二。父亲在水泥厂拉平板车谋生,绳索日复一日地勒进皮肉,肩头的印痕比脚底的老茧更厚更深;母亲守着几亩贫瘠的薄田,春种秋收,汗水摔八瓣,收成也仅够全家七张嘴勉强“塞牙缝”。饥饿与匮乏,是薛卫滨童年最深的底色。
展开剩余85%1999年盛夏,十六岁的薛卫滨初中毕业了。从小喜欢曲艺的他想去艺校上学,可240块一学期的学费让父亲犯了难。在愁眉苦脸和唉声叹气中度过十一天后,父亲嗫嚅地开口:“孩呀,爹没本事,实在拿不出这240块钱……”哥哥弟弟都要上学,薛卫滨理解父亲的难。
父子谈话的第二天,薛卫滨便一头扎进了谋生的风浪中。在县城打零工一个月,他嫌“没意思”。为了赚300块劳务费,他瞒着家人,独自奔向遥远的新疆摘棉花。“阿拉尔的棉田啊,真叫个望不到边!”回忆时,他眼神仿佛又看到了那无垠的白色。
“天不亮就得下地,棉花秆比人还高出一大截,棉壳硬得像刀子,把手指头划得全是血道子。”夜晚,蜷缩在潮湿阴冷的地窝子里,“蛤蟆就在脚底下蹦跶,那滋味……”他摇摇头,没再说下去。这“凑合”的栖身之所,是生存最原始的挣扎。
回村后,命运的线头似乎有了点方向。他拜在一位响器班班主门下。农忙时节,他像牛犊一样挥汗如雨地帮师傅干农活;农闲时,就抱着冰冷的唢呐,吹到嘴唇开裂出血,只为能“凑合”吹出个调调。为了学到更系统的乐理,他不惜借债报名培训班,再用繁重的体力活去抵债。2000年后,歌舞团在吕梁山风靡一时。薛卫滨又跟着团里四处奔波,像块饥渴的海绵,学会了弹电子琴、打架子鼓。
寒冬腊月赶红白喜事,单薄的裤子抵不住吕梁山的寒风。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是从岚县骑摩托到临县清凉寺唱堂会,几十公里的山路,风雨裹挟着严寒,冻得他手脚都失去了知觉。
“那时候是凑合着活了,说是“凑合”,也就是拿命换口饭吃。”薛卫滨总结道,语气平静,却透着千钧重量。
柜顶蒙尘的“柴火棍”与指尖的血泡
2012年,命运抛来一根看似不起眼的橄榄枝。经县文化局推荐,薛卫滨得以拜入临县民间艺术大师康云祥的门下。然而,师傅的拜师条件明确:必须学会弹三弦。这让薛卫滨犯了难,内心甚至有些抵触——在他当时的认知里,三弦是“瞎子讨饭的玩意”,土气又寒酸,哪有吹唢呐登台来得体面风光。师傅郑重赠予他的那把老蟒皮三弦,被束之高阁在他家柜子的顶上,静静地躺了近一年,落满了灰尘。彼时的他,心思全扑在编写秧歌词上,觉得那才是能登大雅之堂的“正经本事”。
转机发生在2014年。薛卫滨心血来潮创作的一个三弦书食品安全题材意外获得客户青睐,对方欣喜之余,要求他本人登台表演。他瞬间如遭雷击——猛然惊觉,自己竟连最基本的弹奏都不会!“这下可丢大人了!”羞愧难当的他,红着脸,踮着脚把落满灰尘的三弦取了下来。为了不露怯,更为了那点不甘的尊严,他开始了近乎自虐般的苦练。每天雷打不动弹练九个小时,手指磨出血泡,挑破了,缠上胶布继续弹。白天跟着唢呐班四处奔波赶场,晚上就着昏黄摇曳的灯光,一字一句地啃唱本、背曲谱。一次在台上,因连日疲惫走了神,竟把唱词记混了,台下爆发出哄笑,那一刻,他“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”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日复一日的磨砺中,薛卫滨渐渐品出了三弦那深沉的韵味。那些曾经觉得“土得掉渣”的曲调,细细咀嚼,竟仿佛藏着黄河奔涌的涛声和黄土高原的厚重与苍凉。2015年春天,在县里举办的非遗展演舞台上,他屏息凝神,弹唱了一段《相国寺》。弦音落定,台下爆发出如潮水般的掌声与喝彩。那掌声,像惊雷一样炸响在他心头,他幡然醒悟:这哪是什么“瞎子的玩意”,分明是老祖宗用岁月和心血凝成的无价珍宝!整整三年苦练,薛卫滨终于能“凑合”出师了。虽然恩师康云祥已驾鹤西去,但他硬是把柜顶上那件蒙尘的“摆设”,磨成了手中最趁手的“兵器”。这把曾被他极度嫌弃、差点当柴火烧掉的乐器,竟成了扭转命运的“金钥匙”——从勉强糊口的江湖艺人,到受人尊重的非遗传承人;从四处漂泊的“野路子”,到站稳脚跟的文化使者。薛卫滨在铮铮琴弦上,用血汗和执着,弹拨出了一曲崭新的人生乐章。
琴弦上的“万年春”与屏幕里的新舞台
清晨的阳光暖暖地洒满薛卫滨精心改建而成的非遗传承工作室。墙上,“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”的证书在光线下泛着庄重的金色光泽。薛卫滨正被一群年轻的面孔围着,他手指灵动如飞,娴熟地示范着“风雨板”的弹奏技巧,铿锵的节奏在室内回响。这里是他非遗传承的基地,也是梦想扎根、薪火相传的摇篮。
案头的工作日程本摊开着,密密麻麻写满了行程:“周三县文化馆授课,周五电视台录制节目,周日晚抖音直播……”薛卫滨的指尖在“文化下乡演出”那一栏上停留、摩挲,眼神温和而坚定——这是他的根,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。前两年,他用政府发放的非遗传承人补助金,加上演出攒下的辛苦钱,购置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。“再也不用骑着那破摩托,顶风冒雪赶场子了。”他的笑容里是卸下重担的轻松。
傍晚的抖音直播间,气氛热烈。观众人数轻松突破五千大关。弹幕如飞梭般滚动,有人问:“薛老师,您现在声名远播,算是成功人士了吧?”他依旧挂着那带着泥土气息的憨厚笑容,指尖轻拨琴弦:“嗨,凑合凑合,混口饭吃。”然而,那眼角眉梢流淌出的满足与自豪,却是怎样也藏不住的。刚下播,工作室的门被推开,二十岁的儿子抱着三弦,兴冲冲地来找他请教。
如今,他的“薛家班”三弦团队已有十多名成员,清一色是慕名而来的年轻后生。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,他们不仅活跃于省市各级非遗展演,更勇于创新,将笛子、中阮、二胡等元素巧妙融入古老的三弦书表演中,让这黄土坡上的“老腔调”焕发出时代的新声。
工作室一角的玻璃橱窗,俨然一座微型的荣誉殿堂:“吕梁市曲艺大赛一等奖”“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”……最显眼的位置,端放着前年参加央视大型文化节目录制时的照片,照片上的薛卫滨,身着整洁的中山装,笑容舒展,眼神明亮,那份发自心底的自豪感几乎要溢出相框。
“现在这日子,凑凑合合挺好。”薛卫滨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,像是口头禅。但朝夕相处的徒弟们、相濡以沫的妻子都心知肚明,这轻描淡写的“凑合”二字里,浸满了半生辛酸汗水换来的骄傲,是苦尽甘来后那份踏踏实实的满足。那把曾经只为“凑合”糊口的三弦,如今正被他的双手在新时代的春风里,奏响着越来越动听、越来越响亮的希望乐章。
古韵新生
七月的吕梁山,黄土烫脚。戏台上,薛卫滨竹板铜铲铿锵,三弦在他粗粝的指下奔涌。汗水砸在台板上,瞬间没了踪影。台下无人知晓,那宽大的演出裤管里,严严实实裹着厚厚的秋裤与棉袜。
演出间隙,阴凉处歇脚。记者瞥见他卷起的裤管下,羊毛袜紧贴着皮肤。“薛老师,要‘三伏天’了,还穿这么厚?”他咧嘴一笑,顺手把裤腿又往上提了提:“老寒腿闹的!年轻时雪地里骑摩托跑场子落下的病根。”他拍了拍腿,语气平常得像说别人的事。“这腿脚是‘凑合’用着。可没这份‘凑合’,也遇不上这三弦的造化。”
“凑合”。这词像一把钥匙,轻轻一转,打开了他四十多年的光阴。
少年时的新疆棉田,望不到头的白。棉壳利得像刀,手指头全是血道子。夜里蜷在渗水的地窝子,“蛤蟆就在脚底下蹦跶”。那是为一口饭的“凑合”,是身体与荒野最原始的搏斗。
后来,恩师递来那把蒙尘的老蟒皮三弦,他嫌“土气”,束之高阁。直到一次演出迫在眉睫,才红着脸取下来。为了那一点不甘心的尊严,开始了苦修。手指磨出血泡,缠上胶布接着弹;昏暗的灯下啃唱本,背到眼皮打架;台上唱错词,哄笑声像鞭子抽在脸上。整整三年,血汗浸透了琴杆。终于,在非遗展演的喝彩声里,那把差点当柴火烧的“柴火棍”,发出了惊雷般的回响。这技艺的“凑合”,是咬碎牙的淬炼,终于触到了祖辈血脉里的黄河涛声。
如今,工作室里证书生辉,案头日程排满,“薛家班”的年轻人围着他转。直播间里,他依旧挂着憨厚的笑:“嗨,凑合凑合,混口饭吃。”可儿子抱着三弦推门进来请教时,他眼里的光藏不住。那身与盛夏格格不入的秋裤棉袜,成了他最沉默也最响亮的勋章。
辞别时,热浪未消。看着他略显蹒跚却稳稳走向戏台的背影,那身“凑合”的装束,在黄土坡蒸腾的背景里,格外清晰。这哪里只是御寒的衣物?分明是半生风雪刻下的年轮,是黄土地里长出的最倔强的根。他用布满老茧的手和裹着厚袜的脚,在“凑合”的表象下,踏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,那弦音里,是滚烫的不屈,是生命的回响,一声声,震动着吕梁山的沟壑。
来源:吕梁日报
责编:张雅璐
发布于:山西省盛达优配-股票配资炒股交流-武汉股票配资平台-加十倍杠杆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